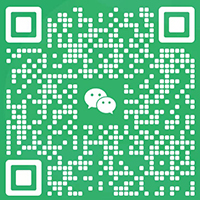3月17日,銀保監會等五部委聯合印發《關于進一步規范大學生互聯網消費貸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。《通知》明確,小額貸款公司不得向大學生發放互聯網消費貸款,未經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機構不得為大學生提供信貸服務。
盡管《通知》也表示,為滿足大學生合理的消費信貸需求,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,開發有針對性、差異化的互聯網消費信貸產品。
但在一些消費金融從業者的理解中,市場空間非常狹窄,退卻才是最好的選擇。
公布后,大學生還能在互聯網消費平臺上貸款嗎?
拍彩晶從不同學校招募了4名學生志愿者,在征得對方同意后,對目前在市場上運營的18款互聯網消費貸款產品進行貸款測試。
令人意外的是,測試的幾家持牌金融機構正規軍統一拒絕了貸款申請,18家平臺最終能順利借到錢的寥寥無幾。
相比之下,不少從業者和學者認為,大學生的消費金融需求屬于剛性需求。然而,大學生客戶群在消費金融領域并不具備“剛需”的尊嚴。隨著新規的出臺,愿意滿足需求的持牌金融機構寥寥無幾。
在此背景下,隱憂在于,如果正規軍毅然撤退,地下校園貸會卷土重來嗎?
01:借用測試
本次測試的4名大學生志愿者分別是北京某學校大二學生A;B,東北某高校大二學生;C,成都某大學大二學生,D,湖南某大學研究生。
從測試結果來看,大致可以分為三類:
類型一:直接拒絕
在測試中,今日頭條、百度、攜程、拉卡拉、分期樂等大部分貸款產品在授信階段直接拒絕了學生的貸款申請。A同學告訴派財經,大部分借貸平臺拒絕的原因是“借款人不符合申請資格”。其中,杜小漫金融“有錢就花”的理由最為明確。其拒絕貸款界面顯示“根據國家監管要求,度小漫不向學生提供貸款服務”。
第二類:中途攔截
學生已經獲得了這些貸款產品的授信額度,但進一步的操作突然中斷,無法繼續。比如小米金融旗下的小米穗行。
經過實名認證、填寫銀行卡號等操作,大二志愿者A獲得了8500元的貸款額度。然而,當他進一步借錢時,卻卡在了“人臉識別”環節。盡管他反復嘗試了3次從頭操作,但界面顯示“身份識別失敗”。另一位測試同學也遇到了與小米貸相同的情況。
第三類:成功借貸
在測試的18款消費金融產品中,4名同學中,大部分人之前都開通過螞蟻花唄和京東白條,可以使用之前的額度進行消費。此外,360欠條、美團生活費、美圖借錢均成功借到現金。其中360借條4次拉卡拉易分期,只有1次因技術問題暫停,其他3次均成功。美團生活費和美圖借錢各成功一次。
根據借貸界面信息,360借條的出資方為金城銀行、百信銀行等,屬于持牌正規軍。美團的生活費資金來自五礦國際信托有限公司,美圖的貸款資金來自武漢眾邦銀行。
從運營和提醒的角度來看,360欠條和美團生活費都為學生設置了關卡。
從利率來看,以12期500元為例,360張欠條到期需要償還602.6元,年化利率為20.52%;美團生活費到期569.2元,年化利率13.84%。
從此次測試的結果來看,平臺在大學生助學貸款的審批上變得更加嚴格,持牌正規軍甚至達到了“一刀切”的地步。
02:燙手山芋
“過去,全國大學生貸款存量普遍集中在幾家龍頭互聯網小貸上。”廣東省小額貸款公司協會常務副秘書長徐北透露。
這份文件對部分地區的大型互聯網小貸公司影響還是比較大的。徐蓓表示,“尤其是大學生貸款業務占比超過60%的平臺,近期將面臨整改轉型等問題。”
“這些平臺最直接的變化就是去庫存、止增、轉變經營方向,”徐蓓告訴拍財經。
需要注意的是,從拍財景梳理測試結果來看,持牌金融機構對學生群體的“阻擊”比小貸公司做的更徹底、更果斷。
在測試的18款貸款產品中,有招聯消費金融、微眾銀行等5家持牌金融機構。這些產品經過了一致的測試,并且在測試學生貸款申請被拒絕時“迅速而溫和”。
北京消費金融銀行在拒絕B(化名)申請的短信中寫道:“綜合評分后,我司暫時無法受理您的申請,希望日后為您提供服務。”
多位持牌消費金融從業者明確告訴拍金融,他們根本不是學生群體。甚至,一位有執照的消費金融內部人士透露,“只要有辦法識別用戶是大學生,一般都會被拒絕。”
其中,最主要的壓力來自輿論。
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黃大志直言,學生信貸的審慎主要源于校園貸的社會負面效應過大。
某持牌消費金融機構內部員工也坦言,他們考慮不做學生客群,輿論風險占了很大比例。
黃大志說,“如果真的出事拉卡拉易分期,輿論風險和監管風險不是公司能控制的,影響太大了。所以很多金融機構寧愿不做,風控卡23歲,屏蔽了大多數學生用戶。”
事實上,“卡齡”是一種阻斷學生客戶的常用方式。
“卡齡可以接受,但也意味著平臺要放棄很多客戶。”消費金融領域從業者周志(化名)表示。比如在一些場景下,分期的用戶更加年輕化,25歲以下的用戶占比為25.近一半的客戶群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,通常是多種條件結合在一起。周志說,比如地址在大學附近,加上學生的年齡,平臺就會拒絕;如果單位填寫了學校和學生的年齡,平臺也會拒絕。
但是,僅通過年齡、所在地等維度,仍然無法準確判斷借款人的學生身份。比如一些研究生、博士生,甚至是大一點的學生,都不會被篩選出來。
因此,“查學信網”是判斷用戶學生身份最實用的方式。
“過去,一些小額貸款機構使用爬蟲從學信網采集數據,”周志透露,“現在正規機構要求用戶對學信網數據進行授權,非常麻煩。一般借貸平臺不會從學信網查用戶。”學信網,如果用戶不是學生,他認為這個借貸平臺有問題。”
周志說,他們也很無奈,“我們其實很難做到。給大學生貸款,監管風險和輿論風險都很高;不給他們貸款,又很難篩選出學生。” . 直卡時代意味著放棄部分用戶。
顯然,大學生群體已經成為一些金融機構眼中的“熱山”。
此前有深度介入大學生的機構表示,他們通過風控手段阻斷助學貸款的成功率達到了98%,目前還在努力中。
03:隱憂
曾幾何時,大學生群體是金融機構眼中的“新太陽”,是一群優質授信客戶。
黃大志說,大多數大學生都超過了18歲,已經長大成人。在大學亞社會,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日常開支,這也促使他們有一些合理的消費需求。
“我們大學生有沒有得罪什么人?華北借給我們的金額是有限制的,比如500、1000……”
校園貸新規出臺后,這條微博熱帖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的心聲。
然而,當輿論聚焦在大學生過度借貸、裸帖等更引人注目、帶來流量的惡性事件上時,這樣的聲音雖然有些微弱,但卻是真實存在的,不容忽視。
志愿者B告訴餅財經:“我們正處在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,想嘗試新鮮事物的階段,成本肯定比以前多了,有超前消費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徐蓓直言:“同齡人中,大學生不僅人數最多,而且消費能力最強,違約成本最高,還款能力最好,尤其是女大學生。”
不少從業者認為,大學生學分是一種剛需,應該得到滿足。而且,大學生的信用行為十分普遍。派財經調查顯示,“花唄”是目前使用最廣泛、最受歡迎的產品。很多精明的同學把花唄當成了類似信用卡的省錢工具。如果按時還錢,就沒有利息,也可以提高資金的流動性。
“我們宿舍4個人,有2個人在用花唄。”志愿者A透露,學校里很多人都在用花唄。
監管也意識到,要滿足大學生合理的消費金融需求。在此次新規中,監管明確需要“開門見山”:為滿足大學生合理的消費信貸需求,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,有針對性地開發差異化的互聯網消費信貸產品,如下:小額、短期、風險可控的原則。
但為什么現在“前門”打開了,原本的優質群體卻不受歡迎了呢?
除了前面提到的輿論壓力和風控難度大之外,嚴控風控下的高成本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例如,新規提到“嚴格落實大學生第二還款來源,通過電話等合理方式確認第二還款來源身份的真實性,取得第二還款來源(父母、監護人)或其他管理人員等)認可其貸款行為并愿意代為償還書面擔保材料,嚴格控制大學生授信資質。”
“大學生一般都是小額借款,這一套手續又費時又費力,吃力不討好。” 一位同修說。
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建議,《通知》關于第二還款來源的執行流程應適當簡化。他表示,規范和完善校園金融市場,需要進一步轉變思想觀念,以科學的態度對待校園金融市場,以適當方式滿足大學生金融服務需求。一方面,金融管理部門采取多種措施,加大整治力度,堅決遏制違法放貸行為的無序蔓延,嚴堵“橫盤”;另一方面,要采取合理有效措施,推動金融機構為大學生提供服務,打開“大門”
如果“前門”被堵住,大學生合理的剛性需求無處安放,就會給“側門”釣魚者以可乘之機。
得到教訓。
2017年6月,銀保監會等三部門發布《關于進一步加強校園貸規范管理的通知》,暫停網絡借貸平臺開展校園信貸業務。短期內,“校園貸”亂象得到有效整治,總體規模回落。
但2019年,央視315爆出“714高射炮”,周期僅7天或14天,年化利率達到百分之百,甚至超過1000%。許多大學生也深受其害。反倒是地下放高利貸的層次更加肆無忌憚了。
派財經也在此次調查中發現了苗頭——非正式校園貸仍在地下悄悄滋生。
“我在廁所和洗衣房看到過借貸的小廣告,”一名新生說。用鋼筆寫的小額貸款廣告。
拍彩晶在微博搜索界面輸入“助學貸”,依然能找到幾十個“助學欠條”“助學貸”的用戶。
顯然,滿足大學生需求的金融需要有社會責任感。黃大志認為,大學生存在一定的弱點,為他們提供信用的產品必須具有普惠性。
然而,當有資格觸碰這個“熱山渝”的正規軍紛紛撤退時,那么誰來滿足大學生群體的合理信貸需求呢?(結束)
搜索關鍵詞:




 拉卡拉微智能觸屏POS機
拉卡拉微智能觸屏POS機
 拉卡拉電簽POS機
拉卡拉電簽POS機
 拉卡拉傳統大POS
拉卡拉傳統大POS
 拉卡拉智能POS
拉卡拉智能POS